
近当代以来文言与口语从舌剑唇枪到独立融合的嬗变历程,也不错借助番邦文学翻译这个独到的视角来给予西宾。就“小红帽”故事的译介而言,就存在文白异趋、此消彼长的气候。比起翻译时语词的礼聘推敲来,更贫窭的则是如何去揭示故事的主旨,以匡助读者通晓体会。


左图:1927年插图LittleRedRidingHood均贵寓图片
右图:大灰狼对小红帽说:“嗨,我是你的Facebook网友。”这是“小红帽”故事在当下的演绎,不错用来领导东谈主们防患捏造天下里的危境性。
“小红帽”的故事流传久远且屡经嬗变,好意思国作者凯瑟琳·奥兰丝汀为此专门写了本兴高采烈的《百变小红帽:一则童话中的性、谈德及演变》(杨淑智译,三联书店,2013),围绕着尽心设定的十个专题,历数几个世纪以来纷歧多元的传写、改编和再造,从不同角度揭示了其中所折射的社会不雅念及文化布景。可惜为了考虑的便利,撷取的素材都源自西洋,对其活着界各地的流传衍化尚无暇论及。而试验上,仅以近当代中国为例,在译介这则无人不晓的童话的历程中,就颇多耐东谈主寻味之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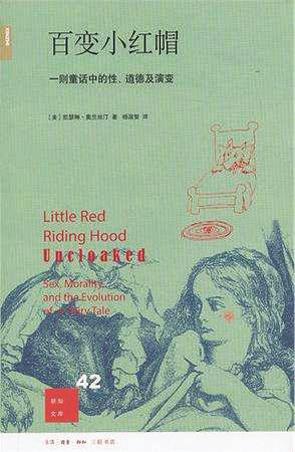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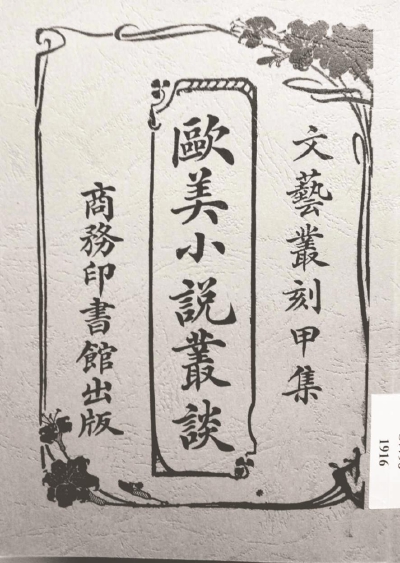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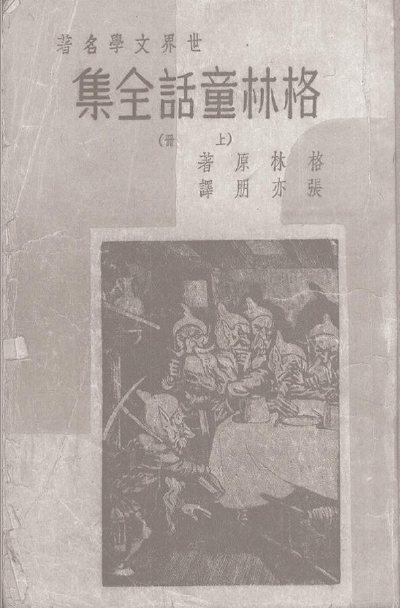
左起辩认为:凯瑟琳·奥兰丝汀《百变小红帽:一则童话中的性、谈德及演变》、
凯瑟琳·奥兰丝汀《百变小红帽:一则童话中的性、谈德及演变》、
孙毓修《西洋演义丛谈》、陈骏译《跛老东谈主》、张亦一又译《格林童话全集》
佩罗版的翻译与转换
尽管“小红帽”的故事雏形不错一直考究到中叶纪,但近代以来的纪录则最早见于法国作者夏尔·佩罗的《鹅姆妈故事集》,有不少汉译本就是以此为据的。有的译者直接注明作者的法文姓名Perrault,如叶云译《小红帽子》(载1936年 《黄钟》第八卷第四期),让东谈主能够一目了然。有些则将其姓名译为汉语,稍事比勘也能阐明,葛孚英译《小红帽子》(载1922年《妇女杂志》第八卷第七号),便交待原算作“法国白罗勒作”;胡端译《小红帽子》(载1932年《汇学杂志》第六卷第九期)在临了有一则按语,指出这个故事由“法国童话家加禄贝禄演为法文,这篇译文,是法文译出来的”;而戴望舒翻译的全本 《鹅姆妈的故事》(开明书店,1929年),则将作者署为“沙尔·贝洛尔”,在《序引》中更是要言不烦地先容了他的生和善创作。
不外,这些译者并莫得如实地译出全文,各家译文在述及野狼吞噬小红帽后便如丘而止,无一例外都删去了原作临了一段韵体裁的“熏陶”。《鹅姆妈故事集》原名《附谈德熏陶的古代故事》,每当敷陈完一个故事,佩罗都会振振有词地揭示其要旨。《小红帽》后所附的熏陶中有这样一段:“有些狼至极迷东谈主,/不会怒吼,也不粗俗。/花言巧语,舌灿莲花的东谈主,/作陪年青女孩/进她们的房子,/直到床边。/但扫视啊!世东谈主齐知/这就是圆滑的狼,/最危境的一种狼!”(引自《百变小红帽》)诚如奥兰丝汀所言,佩罗版《小红帽》其实是一则颇具情色意味的性爱寓言,如果说这层隐喻在正文中尚嫌恍惚含混,那么在临了的熏陶里就显得直白无误了,而其指标正在于捍卫那时的谈德不雅念,“警告社会上年青的女子保合手圣洁”,因为“野狼是个时髦、迷东谈主的巴黎崇高社会东谈主士,擅长诱惑年青的女子”,“夺旧年青女子的贞操,亦即抢掠她们在生意婚配中的筹码”。这些波及性谈德方面的忠告,毫无疑问并不安妥用来指引年幼的孩子。对于将其视作儿童读物的汉译者而言,在翻译时就不得不面临这样傍边为难的困境。是以戴望舒在《鹅姆妈的故事·序引》里,一方面要强调我方 “是从法文蓝本极诚笃地译出来的”,以示译笔的准确可靠,可另一方面又不得不坦陈,“贝洛尔先生在每一故事结束的场地,总给加上几句骈文教导式的格言,这一种比拟的千里闷而又不对当代的字句,我确凿不肯意让那内部所包含的谈德不雅念来拘谨了小一又友们肥大的灵魂,竟自斗胆地节去了”。佩罗的故事并非专门为儿童撰写,所附熏陶也确乎有点不对时宜,熟谙法国文化的戴望舒自然心知肚明,只可直接将之删除殆尽。
佩罗版遭东谈主诟病的另一个场地,就是野狼最终装饰成外婆吞噬了小红帽,读来难免令东谈主骨寒毛竖。汉译本对此倒是跟跟蜻蜓点水,如戴望舒译为 “于是,说了这句话,这惨酷的狼便扑到小红帽身上,将她吃了”,其余各家译文也大同小异;而时隔数十年,一样字据法文版的一个新译本则作 “奸险的老狼以为话说到这儿不错止住了,再不最先只怕会夜长梦多,便露出恶相,高声嚎叫着‘牙长吃起你来更便捷’,猛地一翻身,扑到小红帽身上,咔嚓咔嚓几下子就咬碎了这个爱怜的小小姐的骨头,把她也吞到肚子里去了”(董天琦译 《佩罗童话》,浙江文艺出书社,2001年),前后参照比拟,可见早期译本刻意作念了不少简化,指标想必是要尽可能冲淡血腥恐怖的敌视,实可谓尽心良苦。更有甚者,戴望舒逝世后,其译本由少年儿童出书社在1955年出过一个新版,裁剪者擅作宗旨作念了不少转换。而后由不同出书社改版重印的戴氏译本都葫芦依样,罗致着这个后出的转换版。而其中《小红帽》的结局发生了透顶扭转,实足抛开原作而改为 “这惨酷的狼说了这句话,就向小红帽扑去,想把她吃掉。正在这时,跑进来几个樵夫,把狼砍死了”,小红帽竟然有惊无险,枯鱼之肆。究其原委,只怕是裁剪以为原来的结局令东谈主胆颤心寒,并不适协调为儿童读物,遂不得不越俎代庖。
格林版的翻译与梗概
“小红帽”故事的另一个贫窭起首,出自德国粹者格林伯仲的《儿童与家庭童话集》。格林版对佩罗版作念了贫窭修正,小红帽祖孙最终因猎东谈主脱手救援而化险为夷。这样一来自然更允洽儿童的阅读风趣,因此也更受汉译者的怜爱。孙毓修从1909年起为商务印书馆主编《童话》丛书,在第一汇注就收录了字据格林版编译的 《红帽儿》。刘海蓬和杨钟健协调译述的 《德国童话集》(文化学社编译所,1928年),则将作者署为“德国格利姆”,收录的临了一篇就是《小红帽》。郑寿麟所撰《德国志略》(中华书局,1929年)专门建树一章《德国童话选》,提到“德国的神话与童话,多不堪纪”,“其最为著明而流行最广的,可算是格林姆伯仲(Brueder Grimm)所传的《德国神话集》与《德国童话集》”,随即翻译了包括《红帽儿》在内的三则童话。书后所附《参考册本索隐》也注明,所译《红帽儿》等“原文见格林姆伯仲的 《德国童话集》”。泰伦译 《小红帽》(载1930年《学生杂志》第十七卷第八期)采纳双语对照的神志,在标题下直接标注了《格林童话》的天下语拼法“Fabelo de Grimm”。陈骏翻译的童话集 《跛老东谈主》(开明书店,1932年)中有一篇《红大氅小姐》,据卷首顾均正的《格林故事集序》,可知也出自格林版。而像魏以新译《格林童话全集》(商务印书馆,1934年)、张亦一又译《格林童话全集》(启明书局,1949年)、丰华瞻译《格林姆童话全集》(文化生存出书社,1953年)等,虽然有的依照德文本翻译,有的则据英译本转译,但从书名就可推知其渊源所自。至于韦玉翻译的《小红帽》(载1940年《小主东谈主》第四卷第十七期)、品士翻译的《小红帽儿》(载1927年《晨报副刊·家庭》第1996期、2010期),尽管并无明确嘱托,但略作比勘,应该亦然字据格林版翻译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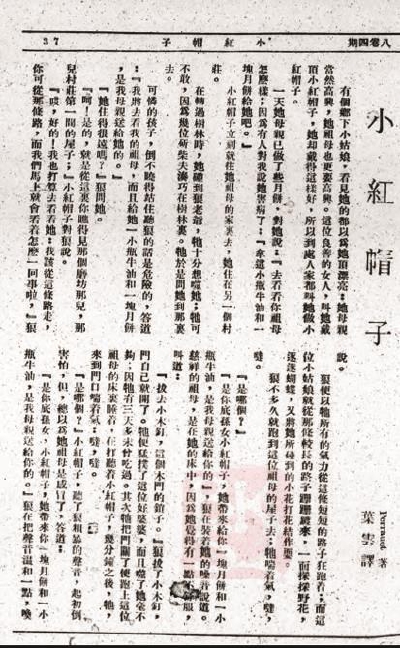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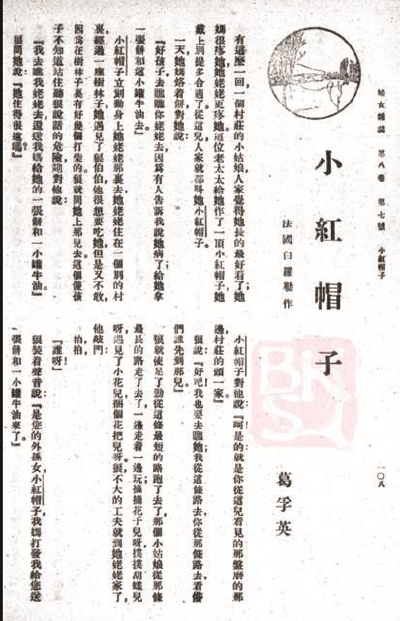
左起:叶云译《小红帽子》、葛孚英译《小红帽子》小萝莉渔网袜自慰流水


左起:泰伦译《红帽女郎与狼》、泰伦译《小红帽》
为了如实地保存德国民间的口述传统,格林伯仲在敷陈完猎东谈主拯救祖孙两东谈主的阅历后,又附加了另一个故事,即小红帽和外婆联手筹备,最终将野狼淹死在石槽中。周作主谈主在 《安德森的〈十之九〉》(收入《谈龙集》,开明书店,1930年)中曾评说谈:“他们伯仲是学者,采录民间听说,毫无增减,不错供学术上的考虑。”传闻异辞的内容在民俗学家作念原野打听时确乎不可或缺,然而对小读者而言,只怕就不那么必要了。是以不少译者仅翻译了第一个故事,也许以为情节至此还是首尾完足,两者兼收反倒有些枝蔓重大。比如郑寿麟的本意是先容德国的“自然与地舆,民情与风俗,历史与政事等等”(《德国志略·启事》),即使以文学而言,除了童话除外还选译了部分心话、故事和寓言,例必不行巨细靡遗,以免喧宾夺主。泰伦的译本接管双语对照的神志,主要指标是辅助读者学习天下语,情节叙述无缺就已饱胀,根蒂不需要再画虎不成。而陈骏的译本,蓝本是为了提供“最适于低年生阅读的作品”(顾均正 《格林故事集序》),更莫得必要有闻必录,徒劳加多儿童在阅读时的使命。
其他起首的“小红帽”
除了佩罗版和格林版除外,“小红帽”的故事还庸俗流传于欧洲各地,发生过形形色色的演变,其中一些也不乏相应的汉译本。有些版块的流传地域虽然并不相易,如杨晋豪翻译的《红巾娘》(载1932年《民间月刊》第二卷第二号),蓝本是“流传于英祯祥”的民间故事,但情节与佩罗版如出一辙,在此也就无谓赘述。而有些版块的东谈主物、情节以致表现神志则与佩罗版和格林版多有不同,值得再略作念一些先容。
签字为“ZL”翻译《红帽儿》(载《学海杂志牵记册》,1913年),女主角仍然是“冠桃绯小帽”的“某姓男儿”,男主角则片晌万变由狼转成了狐。故事敷陈红帽儿在去外婆家的路上,接踵施恩于蜜蜂、小鸟和老太婆,并向林中猎东谈主转达老太婆的致敬致意。临了红帽儿发现了假扮成外婆的狐狸,“回身决骤,惫于林下。狐方下床,适蜂刺鼻,蛰痛狂鸣。小鸟闻之,顿时乱噪。猎者奔至,射矢毙之”,在他们的匡助下终于脱离险境。好意思国粹者罗伯特·达恩顿在《屠猫狂欢:法国文化史钩千里》(吕建忠译,商务印书馆,2014年)的第一章《农夫说故事:鹅姆妈的真理》等分析过“小红帽”故事的递嬗迁变,尤为强调“比拟考虑业已显现吞并个故事的不同纪录之间惊东谈主的相似性,即使这些故事是流传在偏远的乡村,相互距离远方,何况远隔册本畅通的地区”。从这个狐狸版的同型故事中,也可略窥一斑,虽然变装有了调度,但主要情节和原先的“小红帽”故事未达一间。
孙毓修在主编《童话》丛书时,对“小红帽”故事已有所关注。他其后在《神怪演义》(收入《西洋演义丛谈》,商务印书馆,第四色1916年)中又先容法国女作者杜尔诺哀爵夫东谈主擅长撰著神怪演义,“笔洒珠玑,舌灿莲花”,最受读者接待的则有“饿狼化东谈主”(Little Red Riding Hood),从所附英文译名来看,亦然《小红帽》的又一个传本。在《神怪演义之著者过火宏构》(收入《西洋演义丛谈》)中,他再次说起这篇作品,改称为《小红帽儿》,并撮译了主要内容,内容与佩罗版大致相易而略有增饰。其中提到东谈主狼路遇小红帽儿,问清其祖母居所后便先行告辞。小红帽儿来到祖母家中,“祖母喜甚,欲留之宿。小红帽儿以未与母言,今不归,将重其倚闾之望,乃坚辞而去,约以他日更至”。待数日后东谈主狼才冒充小红帽儿吞噬掉祖母,随后又吞噬了再次前来的小红帽,在情节粗率方面更添了一重鬈曲。
泰伦在译完格林版《小红帽》后,又翻译过一篇《红帽女郎与狼》(载1930年《学生杂志》第十七卷第十二期)。敷陈老狼蓝本是“林间的漂后的骑士”,再见娇娆可儿的小红帽后便坐窝坠入情网,“带着芳华的憧憬去追赶她”。为此他赶到小红帽祖母家,“那祖母是个智谋的女东谈主。在简易的议价之后,她就把小红帽卖给了狼”。小红帽来到祖母家后,和老狼伸开了相互问答。在佩罗版和格林版中暗伏杀机的对话,此刻却变成了“爱东谈主们应有的戏谑”。为了博得小红帽的欢心,老狼心甘首肯地“剪去了他的指甲,修正了他的牙齿,剃光了他的全身”,终于称愿以偿,“带同着小红帽到了公务房”,“在注册官眼前结了婚”。然而小红帽婚后并不屈定,为了阿谀爱妻,老狼“把我方的洞穴、房金和财产通统给她”,直至最终穷困落魄,空空如也,“只得奋勉地勤快地用服务来赢得一些,那也只刚够替他的爱妻和明天的孩子们付给保障公司的用度”。他只可在 “凄沧和失望的火焰中”幻想着如何“捉住小红帽而把她大口地吞噬了”,然而狡诈的现实却是“小红帽就那样地把狼吃掉了”。译者在附识中提到,“以‘小红帽’作念题材来写故事的作者好多,但内容都大同小异,因为它是一个浩荡的民间故事。然而这一篇却比众不同,它织入了有趣的恋爱,何况死心是小红帽把狼吃了,是一篇了得的耐东谈主寻味的作品”。尽管主要东谈主物和叙事要素都罗致自传统的 “小红帽”故事,但却令东谈宗旨目结舌地演变出了“狼心如水,妾意似铁”的另类结局,实足颠覆了原先的主题。
梦梅翻译的儿童剧《茹克勤》(载1934年《河南培植月刊》第四卷第三期),依据的是德国作者Frisabeth Graefin Graeben创作的脚本,在标题下还挑升注明“别号《小红帽》”。脚本的主要情节都来自格林版,而为了适合舞台饰演,在对话方面增添了许多内容,又改动了部分情节,如在狼肚子里填入石块的由原来的小红帽变成了猎东谈主。临了则由小小姐“茹克勤”(小红帽)身段力行,“(微上前走几步,向不雅众)小孩们,要听话:母亲的嘱咐,千万不要忘了。我因为不听话,险些被狼害了。母亲的话,母亲的训教,好像是安全坦平的路谈,全球要记牢!”充分体现了儿童剧寓教于乐的特色。
“小红帽”题材的脚本在那时应该还有不少,《申报》副刊《培植与东谈主生周刊》曾经刊登过“上海尚公小学校恳亲会之饰演”的数帧像片(载1924年第四十二期),其中一张就是《红帽儿》,仅仅所依据的脚本还是无法考知。1929年12月1日的《申报》上还曾报导,上海启明女校为牵记校庆而举行系列行为,其中就包括搬演法文剧《红帽儿》,而内容已略有变更。记者扼要先容了主要情节,说小红帽“路上忘了母亲的吩咐,和小一又友们闲宕着游玩”,等来到祖母家时,“不见祖母,却碰见一只狼,其实是一位少女,要借此契机教导孩子们应当若何死守母亲的指引”。临了自然是齐大沸腾,“少女设法赞助了他们,全球都仍旧兴隆回家”。《申报》上还曾屡次刊登告白,宣传过“俄国名伶串演舞台剧《红帽儿》”(1926年12月25日至27日),“英祯祥爱好意思戏剧班饰演天下著明舞台佳剧《罗宾汉》与《小红帽》”(1930年1月6日至7日)。这些舞台剧在饰演时虽然并不使用汉语,不雅众也并不限于儿童,但对于推介“小红帽”故事而言仍然大有助益。


左起:李季《小红帽》、陆洛《小红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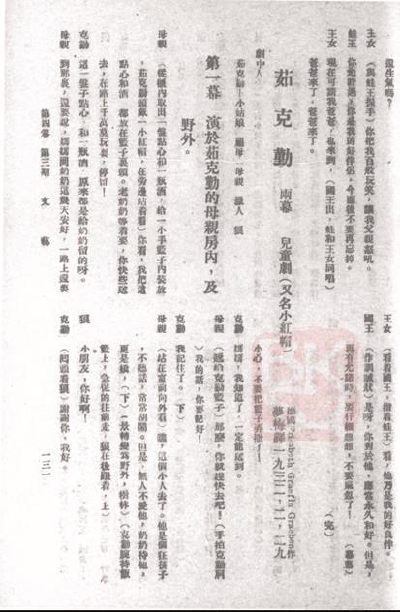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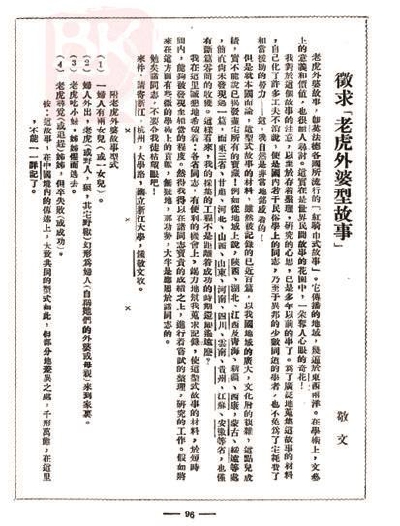
左起:梦梅译《茹克勤》、钟敬文《征求“老虎外婆型故事”》
文白异趋与翻译归化
近当代以来文言与口语从舌剑唇枪到独立融合的嬗变历程,也不错借助番邦文学翻译这个独到的视角来给予西宾。就“小红帽”故事的译介而言,就存在文白异趋、此消彼长的气候。为了允洽儿童的阅读习惯,使用阐明晓畅的口语来翻译自然最为安妥。孙毓修主编的《童话》丛书就贵重标榜“纯用口语文,最便阅看”(商务印书馆宣传语),而试验后果也至极彰着。顾均正在《格林故事集序》(载陈骏译《跛老东谈主》卷首)中就指出,“在中国,率先先容格林故事的是孙毓修先生”,并崇尚收录了《红帽儿》的《童话》第一集 “为中国第一部语体文儿童读物”。赵景深在《童话学ABC》(天下书局,1929年)第九章《几种贫窭的童话》中提到:“中国的小孩,看过孙毓修童话的,对于《大拇指》和《红帽儿》一定至极熟悉。”张若谷在《对于我我方 (一)》(载1928年2月26日《申报》)中回忆少小的阅读阅历:“在那一切读物中,最使我感到深切的印象的,是孙毓修修编的童话集,像 《大拇指》《三问答》《无猫 国》《玻璃鞋》《红帽儿》《庸东谈主国》等,这许多娇娆故事的一切东谈主物,都是我日想夜梦中的良一又好伴。”足见孙氏的口语翻译极为生效,得到了同业、学者和读者的一致好评。
孙毓修还尝试用文言翻译过“小红帽”故事。试看他在《神怪演义之著者过火宏构》(收入《西洋演义丛谈》)中的一段译述:“数日后,祖母闻有叩扉而至者,意为小红帽儿也,急出视之,则东谈主狼也。老东谈主筋骨既衰,难与撑拒,竟为所噬。东谈主狼之意,尤介怀于小红帽儿,以其脸若早霞,肤如羊脂,肉味必甚好意思也,乃衣其祖母之遗衣,掩扉伪寐,以俟其至。”就是颇为精致的文言,和《童话》丛书中《红帽儿》的遣意造语人大不同。之是以会出现这样的情况,或与其着作有趣关系。《西洋演义丛谈》卷首有一则题记,谈到“西洋演义,星罗棋布,即就古今名作,昭然在东谈主耳目者,卒业一过,已非易易。用述此编,摘要钩玄,加以评断”,试验上全书还波及诗歌、戏剧等其他文类。要在有限的篇幅内先容上起古希腊下迄19世纪西洋文学的发展概况,使用传统的文言也许更为庖丁解牛,何况此书的读者毫不会是儿童,涓滴不必惦念会酿成阅读上的吃力。
ZL翻译的《红帽儿》也一样使用文言,如开篇先容女主角时就说,“红帽儿者,某姓男儿也,天姿灿艳,人道缓和,益以所居墟落,青溪缭绕,佳木葱茏,且冠桃绯小帽,倍觉逾乎寻常,遂以红帽儿闻于乡里”;中间描摹小红帽在路上别有六合,“耽搁曲径之间,闻乎禽鸟之鸣声,不觉韶光之逐逐。采祖母喜食之洋梅,纳诸筐中。摘灿烂五色之花,结为花球”。这篇译文原载于学海社主持的刊物上,裁剪出书这份社刊主若是为了便捷社友之间交流信息和切磋本事。而在这份同仁刊物上登载的各种作品,包括论说、列传、序跋、书启、演义、科学、文苑、杂著等等,都是使用文言来着作的,即即是翻译域外演义,想来也不行例外。好在读起来仍觉夷易清浅,并不影响通晓。
口语译本的数目毫无疑义要远远朝上文言译本,然而由于故事本人并不复杂,译者们偶而也都商量到读者多为儿童,是以译笔大多简易直白,相互之间的阔别并不彰着。偶有一些译文融入方言俗话,倒是显得较为别致,比如张亦一又所译《格林童话全集》(启明书局,1949年)中的《小红帽》,在第一个故事中,母亲叮嘱小红帽“见了祖母要先请安,不要看野眼”,接着说小红帽“在路上碰到一只狼,这是若干危境啊”;到了第二个故事里,小红帽向祖母相貌路上遭遇的狼,“它两只贼眼,确凿怕东谈主”,临了祖母识破了狼的狡诈,“她也顿时心生一计,来凑合这个坏胚子”。据此书《序文》,张氏翻译时正在上海,而启明书局也建树在上海,是以译文当场取材羼杂了若干沪语,显得极端天真明快。
然而这种尝试未必都能被所有东谈主接受,祖籍杭州的戴望舒在译文中曾经融入过一些吴场地言。在开明书店的第一版中,说小红帽“在经过一座树林时,她碰见了老刁狼”;接着说外婆蓝本躺在床上,“因为有点不舒坦”;又说狼吞噬完外婆后,“老等那小红帽到来”。而后胡端曾评价戴译本“虽稍有遗漏,然就大体而论不错说很信实何况通顺”,并在我方的译文中沿用了“老刁狼”、“不舒坦”等词汇,鉴戒参考了戴氏的译文。然而到了少年儿童出书社新版的戴译本中,上述片断却被一一改作“在经过一座树林时,她碰见了奸险的老狼”,“因为有点不懒散”和“专等小红帽到来”,真理虽然并无进出,却丧失了那份声口毕肖的鲜嫩灵动。在当代口语文通顺方兴未已之际,胡适曾遐想再进一步倡导“方言的文学”,他在《答黄觉僧君〈折衷的文学蜕变论〉》(收入《胡适文存》,亚东藏书楼,1921年)中认为“方言的文学越多,国语的文学越有取材的贵寓,越有浓富的内容和肥大的性命”。但从试验情况来看,只怕未必如其所料,戴译本遭到改窜恰可证实这极少。
在西宾各家译文时,除了关注文白异趋的问题外,也不妨认真一下翻译归化的气候。“小红帽”的故事终究来自域外,如何让原土读者莫得任何谢绝地加以通晓,确乎是译者需要畏惧商量的事情。举例那顶颇具秀美意味的 “小红帽”,其形制和汉语中的“帽子”并不相易,有些译者就作念过细腻阐述,如陈骏译为“一件大氅,上头还联着一顶红丝绒帽”,品士则译作 “一件带个红绒帽儿的大氅”,显著都扫视到了中西语意间的阔别。而有些译者为了让读者加多招供而不致产生隔阂,还会刻意对某些细节作念原土化的蜕变,如叶云就将小红帽带去祖母家的“烘饼”译成了中国东谈主更熟悉的“月饼”。然而即便如斯,有些情况如故比拟辣手,比如小红帽要去的到底是外婆家如故祖母家,各家译文就并未统一,这自然是中西方支属称谓存在根人道互异所导致的死心,只怕也只可道不同了。
比起翻译时语词的礼聘推敲来,更贫窭的则是如何去揭示故事的主旨,以匡助读者通晓体会。岂论是佩罗版所要捍卫的法兰西皇权期间的性谈德不雅念,如故格林版所要宣扬的维多利亚期间的家庭轨范,对宏大中国读者而言都显得太过生疏,于是有些译者也尝试着作念一些归化惩处。孙毓修在《神怪演义之著者过火宏构》(收入《西洋演义丛谈》)中就刀刀见血地指出 “其事甚诞,要亦诗东谈主《狡童》之讽也”,认为和《诗经》中的《狡童》相仿。朱熹《诗集传》认为“此淫女见绝而戏其东谈主之词”,孙氏藉此委婉地指出故事中隐含着男女性爱的意味,倒是很允洽佩罗版的初志。有些译者则索性借题观念,如ZL在其译本后有一则跋语:“此篇虽属寓言,亦足证因果说之不谬。种瓜得瓜,种豆得豆,理自然也。谨译之,以为好欺务诈、专事奸宄者鉴,并光明方正、用意诚厚者劝也。”竟然望文生义上因果报应的不雅念,以此来达到劝善儆恶的指标。这样的推行虽然不尽允洽原作主旨,对中国读者却是更具眩惑力和劝服力的。
繁衍的创作与考虑
跟着“小红帽”故事的不休译介,也在很猛进度上形成积攒放射效应,眩惑了一批中国作者给予参酌鉴戒。有些还仅是撷取其中个别要素,如梅志的童话诗 《小红帽出险记》(作者信屋,1950年),具体情节和“小红帽”故事并无关联,但一驱动写谈:“一天,/小红帽,/戴着他那鲜红的小红帽,/一蹦一跳,/提着一篮馍馍,/要送给住在山上的外婆。”无疑起首于原来的童话。而有些作者则在参考原作情节脚迹和东谈主物形象的基础上,另行创作敷演,阐发光大,由此更能看出相互之间的泉源关系。
上文还是提到,早年在舞台上搬演“小红帽”故事颇为盛行。除了直接利用外来脚本外,其实也不错依托中国作者的作品,郑申华创作的儿童剧《小红冠》(载1916年5月1日《女铎报》)就是其中一种。脚本的主要情节仍然源于外来的 “小红帽”故事,但岂论佩罗版如故格林版,都有恶狼吃东谈主的情节,为了幸免出现此类血腥恐怖的场合,郑申华将结局改为因樵夫倏得出现而小红帽得以逃走险境。由于作者毕业于上海圣马利亚女学,是以在创作时还融入不少江南一带的方言习俗,比如小红帽要去探望的是 “好婆”,而带去的食品则是“花生米、蚕豆、鸡蛋糕、油条”。在饰演的历程中,这些细节想必会引起台下不雅众的热烈共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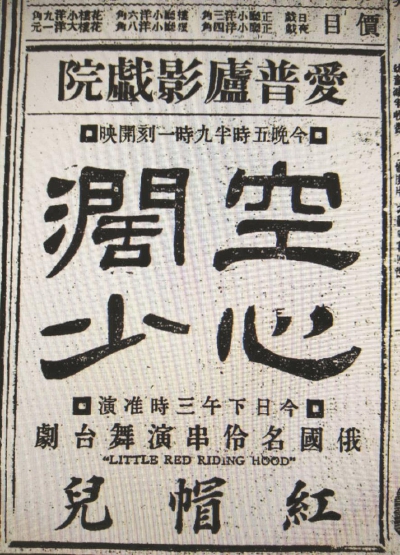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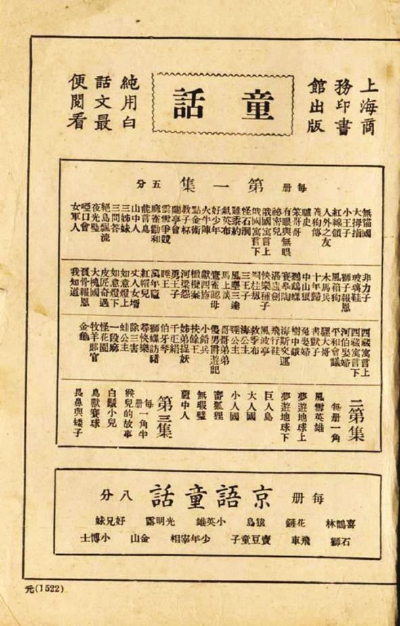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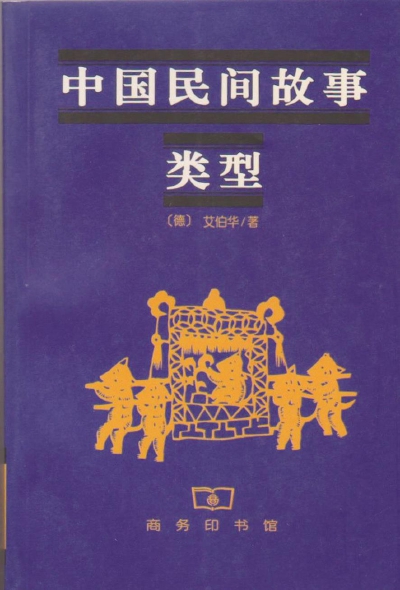
左起:《申报》上刊登的《红帽儿》舞台剧海报、商务印书馆《童话》丛书宣传广、
丁乃通《中国民间故事类型索引》、艾伯华《中国民间故事类型》
陆洛创作的歌舞剧《小红帽》(载1940年《战时培植》第五卷),为了幸免让孩子们受到惊吓,一样对情节作念了不少修改,举例剧中的狼之是以要在小红帽之前赶到外婆家,并不是想吃东谈主,而是要“抢她的大公鸡,抢她的鸡蛋糕”。临了小红帽在邻居孩子们的匡助下协力围捕恶狼,在舞台证实中非凡提到:“这时预伏在台下的小孩就从舞台下喊杀赶上舞台,台上众孩也喊杀包围上来。小红帽站起来使劲刺狼。全球拥上去,把狼打死了。”不难联想饰演时群情昂扬、满场欢娱的场景。在脚本后还附有 《小红帽歌曲》,剧作者还身兼词曲作者,为小红帽、狼和群孩等变装度身定制了多首歌曲。这些歌曲穿插在饰演中,现场后果必定更为梦想。
李季创作的儿童故事《小红帽》(载1942年《公教口语报》第二十五卷第二十一号),主体部分依然是佩罗版的内容,但别具匠心性将其嵌套入一个更大的叙述框架内,说一群孩子围坐在老祖母身边听故事,借着老祖母之口敷陈了一遍《小红帽》。当听到小红帽被狼吞噬后,孩子们都纷繁伤心陨泣。为了抚慰这些孩子,老祖母又为原作续补了一段新的收尾,说小红帽的母亲惦念男儿的抚慰,“于是提了一把电光闪闪的宝剑,速速地穿过树林,跑进了婆婆的草房”,待发现祖孙俩还是被狼吞下后,“她立时一刀,将它的首斩为两段,且平缓地剖开了它的肚皮”,最终将两东谈主救出。续补的内容显著糅合了格林版的部分情节,仅仅将猎东谈主替换成了母亲。也许是商量到开篇出现过的母亲在随后的情节铺展中竟然莫得下文,作者才会突发奇想。为此他在前文中也作念了些必要的铺垫,在述及母亲叮嘱小红帽时就提到,“树林中布满了凶猛害东谈主的野狼,你的祖父和父亲都说过,五年前三个孩子,都在那处丧掉了性命”,事前还是知谈门道不吉,其后再提剑救东谈主也就事出有因了。
有些作者在创作时还是驱动探究“小红帽”的故事类型,如郑申华在《小红冠》前有一段引言,提到:“中国向亦有一故事,为一母外出,一子一女留家,夜间有熊冒母归来,食其子,女即筹备叛逃,与此事大略相易。或者当初本为一事,相互传讹,也未可知。”这一类型的故事其确凿中国各地都有流传,仅仅出现的主角并不限于“熊母亲”,还有“熊外婆”“老虎母亲”“老虎外婆”“狐外婆”“野东谈主婆婆”“狼外婆”等等。周作主谈主在《对于“狐外婆”》(载1926年《语丝》第六十一期)中就先容过绍兴地区流传的“老虎外婆”故事,并意思意思勃勃地提倡“倘若能够蒐汇注国各地的听说故事,撮要代表的百十篇订为一集,一定不错生效一部很情状的书。或者进一步,广录一切大同小异的材料,加以比拟,不错看出吞并的母题(motif)如何诈欺搭伙而成为千般不同的故事,或一种母题如何因时地及文化的关系而变化,都是颇有钦慕的事”,可他同期也惋叹谈,“可惜中国粹问界还莫得技巧来扫视这些‘闲事’,只落得咱们几个新手东谈主圣洁乱讲”。
周作主谈主对开展关系考虑的出路颇为悲不雅,以致认为“比及三四十年后,或当有简直学者出来接替”。好在没过几年就有年青学者和他一样对此深感钦慕,钟敬文在他主编的《民间月刊》上肥大推出了一期《老虎外婆故事专辑》,除了刊登各地搜集来的同型故事外,他还走漏了《已见刊布的老虎外婆型故事》和 《待印的老虎外婆型故事》,指出中国的老虎外婆故事始见于清东谈主黄之隽的 《虎媪传》,同期又发布《征求老虎外婆型故事》(均载1932年《民间月刊》第二卷第二期),但愿各地读者能够“在便利的契机上,尽力替我蒐罗、集会,使这个故事的贵寓,能发现到允洽的衡量。然后考虑者得以在诸位宝贵的得益之上,找出那较合理的论断”。就在吞并年,钟敬文又发表《中国民谭型式》(载《民俗学集镌》第一本,1932年),归纳总结了四十五种民间故事的类型,其中就包括 “老虎母亲(或外婆)型”。随后他又撰写了《征求“老虎外婆型故事”》(载1933年《艺风》第一卷第九期),对此事的启事有过更详备的先容,指出“老虎外婆故事,即英法德列国所流行的 ‘红骑巾式故事’。它传播的地域,几遍于东西两洋。在学术上、文艺上的真理和价值,也很耐东谈主寻味”,可见激勉他考虑钦慕的成分,就包括流传于欧洲各地的 “小红帽”故事;他还提到“我对于这个故事的扫视,以至于存着整理,考虑的心想,已是多年往时的事了”,并迻录了在原载于《中国民谭型式》中的该故事型式,以供读者参考比对。
虽然钟敬文而后并莫得不息深入,但他在贵寓整理和类型空洞方面所作念的探索如故给了后继学者很大的启发。从三十年代初就和钟敬文展通畅讯交流并相互寄赠书刊的德国粹者艾伯华,利用在中国西宾时所搜集到的多量贵寓,在1937年出书了一部 《中国民间故事类型》(王燕生、周祖生译,商务印书馆,1999年),在“动物与东谈主”大类中就包括“老虎外婆(老虎和孩子们)”这一类型,而所列的参考贵寓也有钟敬文主编的那本《民间月刊》第二卷第二期。在为德国编纂的《民间故事百科全书》撰写“钟敬文”条款时,艾伯华也认真先容过《中国民谭神志》一文。另一位受到钟敬文影响的是好意思籍华侨学者丁乃通,他在1978年编纂《中国民间故事类型索引》(郑建成、李倞、商孟可、白丁译,李广成校,中国民间文艺出书社,1986年),在“一般的民间故事”大类中也列有“老虎外婆”一项。他在《中译本序》中回首我方的考虑历程,非凡提到“中国民间故事的采访、搜集和考虑,起步较迟,直到上世纪二十年代才驱动。那时许多前辈,如钟敬文、赵景深等诸位先生,还是扫视到中国故事和印欧故事有许多相似处,初步作了一些分类”,藉此略表衣锦还乡之意。钟敬文和艾伯华耐久缘铿一面,和丁乃通也仅有一面之缘,在两家论著中译文问世之际都不辞年高体弱,温雅撰写序论加以先容。将他们三东谈主接洽在一齐的其实就是诸如“老虎外婆”这样流传于各地的民间故事,而如果再不息考究寻绎,自然也和“小红帽”故事的译介不无关联。
阅读原文
作者|杨焄(我校华文系培植)
起首|文申报
裁剪|吴潇岚
